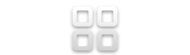我们要唱歌
张俊
1975年国庆节后的一天,一辆老旧的解放牌大卡车将我拖到了潜江县熊口公社马场大队,这是我下乡插队的地方。我是中国第一冶金建设公司的子弟,我们这个点安排的是三男三女,大概上头考虑到我们要在这干一辈子,未来夫妻配对的事都想好了,结果是三年知青生活结束时一对都没配上。

2019年夏,与当年一起下乡的知青重返马场
那天的晚饭是我下乡时吃的第一顿饭。六个人围着一张小方桌,谁都不说话,眼珠子只偶尔转一下。桌边的一盏煤油灯照着三四碗菜,其中一碗是青椒做的酢胡椒,不知谁学着潜江话说了句:哈(吃)啦、哈啦!那个菜还有点好吃,从此让我爱上了这道江汉平原的土菜,只要一看到就会自觉地伸筷子去“哈啦”!
乡下的劳动单调而枯燥,一日复一日,从早到晚也就是那点套路的事。我们跟村民之间都没弄清谁是主要人物。农民说:毛主席说哒,知识青年到农村去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!而我们则说:毛主席也说哒,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。说是这么说,但队长是农民,我们还得服他们管。
乡下的夜晚很长,但却并不难熬,因为通常情况下一吃完晚饭,我们三个男生寝室里的“小喇叭”就开始广播了。“小喇叭”叫方强,他从家里带来两本《战地新歌》歌曲集,差不多每晚他都会端坐在方桌前,借着煤油灯光,从头到尾翻着歌集一首接一首地唱,演播时间一般在一小时左右。他唱时摇头晃脑,得意忘形,偶有唾液飞出却从不喝一口水,不得不让人佩服他的底气十足。
他唱累了就吹口琴,琴声一起,住在隔壁的三个女生就开始跟着哼歌,声音先是细细地,有点羞涩,而后就越来越大,达到三重唱的高潮。

当年的老房子还有几间
我们知青点的人唱歌,其他点的人也唱歌。但我们只唱《战地新歌》里的歌,可别的点里居然有人唱《敖包相会》,还有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。这样一来问题就严重了,这些是资产阶级的歌,我们红色知青是不能唱的。
一天,带队的金干事通知厂里所有下乡的知青第二天一早到我们点来开会。丁干事四十来岁,头发有点卷,不喝酒鼻子也是淡红的。他说一口黄陂话,平时笑嘻嘻的,可训起人来却充满火药味。那天开会,大家都在房前的堤坡上席地而坐,只有他站在堤顶上尖着嗓子喊:《敖包相会》是大毒草,你们不知道吗?嗯,还什么阿哥、阿妹情意长,流水哗啦哗啦响,真不要脸,以后不许再唱!
我们还有个带队的女干事姓江,只比我们大几岁。她身材娇小,肤白发黑,有双梅花鹿样的眼睛。有次见她在水塘边和我们点的几个女知青在一起洗菜,那天她穿件卡腰黑灯芯绒衣,雪白的衣领翻在外边,长辫子背在背上,挽着袖子的胳膊白得像玉石,银铃般的笑声荡过水面,直往人心里落。
江干事那天也讲了几句,她说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》是苏修的歌,要大家以后不要再唱了,要注意政治影响。回城后我还见过江干事,她在工会工作。她的命不好,五十多岁时死了老公,一个男的对她很照顾,她也想再嫁,可那男的却不愿娶她,不久她也病死了,大概还不到六十岁。

在当年的老房子前见到当年的乡亲
我以前没听过金干事说的那两首黄歌,散会后就让别队的知青唱给我听,那优美的旋律一下子就迷住了我,我学会后竟成了我的保留曲目。我发现这样的歌不仅可以使日子变得不乏味,而且那软绵绵的曲调还能给我带来很大的力气。
那年夏天“双抢”时节,打谷场上的脱谷机日夜都在突突地响,噪声吵得人心烦意乱。一天夜晚,由我拖板车负责将装满谷粒的箩筐往仓库里送,那空荡荡的仓库里只吊着一盏马灯,风吹来似有无数的鬼影藏在谷堆后狞笑,等着我给他们送去大餐。我有点害怕,不到仓库门口就开始大声唱歌给自己壮胆:阿哥、阿妹情意长啊,好像那流水日夜响……我一边唱一边将百把斤的箩筐搬到谷堆顶往下倒,那沙沙的流动声仿佛是伴奏的沙球,还怪好听的,歌声中那鬼影也不知跑哪去了。
1977年的冬天,队里派我去洪湖打堤,我是和邻队的王大国等人一起坐一辆手扶拖拉机去的。开拖拉机的叫浩文,是我们队里的一个村民,他三十来岁,长得比我还矮,黄脸黑牙,一张元宝嘴很会唱小调。他那天心情很好,一边开拖拉机,一边迎着冷风放声高唱:妹妹呀,你跷起了白胯子,就打着我的头呀……他的腔调阴阳怪气,但却很有味道,尤其是能引人畅想。后来我才知道他唱的是江汉小调,在咱江汉平原流行了好几百年了。

和当年的知青在马场桥上
我和大国他们坐在车厢里,车里装满了红薯和萝卜,还有一只用麻袋装着的半边猪肉。前几天队里的一头母猪莫名其妙地死了,队长说送到堤上给打堤的人改善生活。我把那只麻袋当沙发坐着,大概是浩文的歌让我们兴奋,我们就拿起红薯或萝卜当手榴弹不停地去“炸”路边房屋里的人,他们若是气喘吁吁地追来,浩文就加大马力狂奔,我们还用“手榴弹”迎头阻击他,让他躲避不及中弹,最后不得不在怒骂中怏怏而去。我们就是在浩文的歌声中一路干着坏事,十分开心地到洪湖的。
我们住的地方是用油毛毡搭的一个窝棚,地上铺着稻草,中间走路,人睡两边,约有三十好几个。窝棚里没有窗子,脏衣服臭袜子的气味,还有煤油灯的气味在里边长久不散,加上又是在湖边,我总感觉窝棚里湿乎乎的。
我们每天凌晨五点就得起床,早餐是木桶蒸的白米饭 ,配萝卜辣酱,三口两口地吃两大碗就得匆匆赶往工地。
洪湖大堤工地像条巨龙,堤项插满红旗,堤上挑土的人上上下下就如同一大群蠕动的蚂蚁。隔十多米远就安有一只高音喇叭,整天不停地放“下定决心,不怕牺牲”一类的语录歌,那阵势震天动地,就像是打大仗前的动员一般。
我们的任务是每天每人挖两方土,自挖自挑,挑着土担子走二十多米远,再爬一个七八米高的堤坡,然后将土倒在堤顶上,由压路机将土块一层层地碾平。
我初去时挑担不会换肩,头几天挑下来左肩又红又肿,然后又变青,一摸钻心地痛,但熬过十多天也就好了。
收工一般是夕阳西下时。吃过晚饭,农民们在窝棚里打朴克赌博,我们几个就来到一排老柳树下听一个叫李方的知青唱歌。
李方也是跟我们一起下乡的,人长得高大,但皮肤粉嫩微红,像个模样俊秀的女人,特别是走起路来屁股有点扭时更像。他在家是独子,老母亲很宠爱他,还让他跟人去专门学过唱歌。他也真有副天生的男高音嗓子,那歌声不比唱《咱们工人有力量》的刘秉义差多少。

见到了当年村里的回乡知青朋友
待我们一坐在地上,说声李方你唱,他就会快步走到我们面前,稍酝酿一下情绪后即进入舞台演唱状态。
这时的李方神情庄重,仰望天空,双眸有光,一曲《延安颂》在他鲜红的双唇间深情地响起,而后在几棵老柳树间长久地回荡。他唱姿挺拔,台风极佳,唯一不足的是他偶尔会情不自禁地翘一下兰花指。
他一般会连唱几首,我们若没听够,还可以点他唱《我站在金色的炉台上》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等。直到他高音突然跑调,摆摆手说我实在唱不动了,我们才会放过他,回窝棚睡觉。说真的,李方的歌声让我能忘记肩膀的痛疼,原来歌声是可以疗伤的。
我们队里的知青都爱唱歌,且都自认为唱得很棒,直到1978年夏遇到一个叫刘子魁的吉他手,这才知道什么叫唱歌。
那是初夏的一个傍晚,我正在知青点的门口无所事事地东张西望等着吃晚饭。突然间发现木桥那边走来两个人,一人是高个子,敞着衬衣,戴看顶白色草原骑手帽 ,走路的姿势很洒脱,他旁若无人的样子就像一个地主在自家庄园里巡视。他旁边的那个矮小略胖,留着小平头,肩上扛着一把吉他。矮个子紧跟高个子的样子很像唐吉诃德和他的忠实仆人桑乔。
待两人走近了,这才发现都是认识的。高个子叫刘子魁,和我住一个街坊,知道他打架厉害。他皮肤白净,留着黑胡子,一笑一口白牙。这家伙长得太英俊,现在想来有点像《泰坦尼克号》里的男主角。另一个叫王一平,是我读初中的同学,他有一双肥脚,人送他一个绰号叫大板。他俩是去另一个地方路过我们这里,因为认识方强就进来吃个便饭。
他俩一进屋,一平就从斜挎的军帆布包里摸出一只奄奄一息的母鸡,他笑嘻嘻地说:刚踩的,还是热的。他让方强交给点里的女知青拿去炖了。

当年在荆州城买的吉他
子魁坐在桌边的一条长凳子上,一只腿曲蜷着踩在上面。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,先是抽了几根游泳牌香烟,喝过一平揣来的一碗水后就抱着吉他开始自弹自唱。
刚开始屋里的气氛有点压抑,我们不知这两个坏家伙来这干啥。我们点三男三女全是良民,除了偷过农民的一点菜外,连鸡毛都没摸过一根。那一刻,我真有点鬼子进村的感觉:子魁是皇军小队长,一平是汉奸,吉他是把可杀人的新式武器。
但随着子魁的弹唱,这一切全变了。烟雾中的子魁影子朦胧,弹吉他的姿态很好看。我是第一次听活人弹吉他,子魁的嗓音低沉浑厚,非常有磁性。他先唱的是南斯拉夫电影《桥》里的插曲《好朋友,再见》,随后又唱了美国民歌《老黑奴》。那伴奏的和弦时而欢快热烈,时而又苍郁深沉,这家伙的情感变化太快,房里压抑的气氛早已随着歌声飘出了窗口。这时天已经黑下来,夏虫还没有开叫,我们都被他的歌声深深地迷住了。
不一会鸡汤端上来了,一大钵冒着热气。子魁摆摆手说:你们吃吧,老子吃腻啦。看着点里的人狼吞虎咽的样子,子魁只是微微一笑,他不吃饭,只是一个劲地抽烟。还没等我们把饭吃完,过足了烟瘾的子魁就站起身来,朝前抡一下胳膊,大摇大摆地出了门。一平也赶紧扛起吉他紧随他而去,夜幕很快就将他俩的身影给吞没了。
他们走了,屋里安静下来。我突然觉得这房里死气沉沉,似乎觉得我们这几个老实的家伙活得也太安份、太憋屈了。
那一夜我有些失眠,子魁的影子老在我眼前晃悠,特别是他那好听的吉他声一直在我耳边响着,像山中叮叮咚咚的溪水声。
我那晚下了个决心:一定要买把吉他。那一年分红,我分了一百二十块钱。在一个下午,我在潜江浩口的公路上扒车去了趟荆州城,在那花六十块钱买了把红棉牌吉他。
几十年来那把吉他一直陪伴着我,每看见它就会想起在下乡时唱歌的那些情景,也仿佛听见刘子魁在小声地说:活轻松些,不必太守规矩。苦恼了可别叹气,我们要唱歌,一切都会好起来。
(作者系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)
打赏
 客服热线:
客服热线: